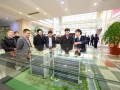日前,由于国家能源委会议释放出核电松动的信息,相关媒体围绕核电存废、内陆核电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国研中心王亦楠老师的《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附于文后)的文章观点最为鲜明,引起了诸多共鸣和争论。现针对王老师文中提出的几点理由,稍谈一点个人认识,以与商榷。
第一,关于核电安全技术问题。
王老师认为即便核电发展历史更久的欧美尚不能保证核电的绝对安全,况乎核电发展史更短的中国?王老师甚至从一个语义学的角度提出质疑,“可以”不等于“已经”。这一点上,王老师言之有理。核电从一代、二代、二代半到现在的三代,正是从“不可以”到“可以”一步步走过来的,无限接近但仍未“已经”。
但我想列举几个数据以供参考: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直接间接造成12000人丧生;2012年底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当年全世界有38.75%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中国。在2010年,空气污染导致了中国124万人过早死亡,其中,14万居民的肺癌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
第二,关于核燃料的对外依存度问题。
诚如王老师所言,我国目前核燃料对外依存度高达85%,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对此,我有两个疑问:其一,以85%的对外依存度高位,会否因为停建或少建几座核反应堆而降低,从而消除这一隐患?短期看应该不会。第二,国际核燃料市场会否发生根本性变化?
铀资源确因其与核武器制造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根据国家对于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当前世界秩序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换言之,国际核燃料市场基本格局不会大变,仍按照市场逻辑正常运行,我们要做的是掌握并充分利用现有市场规则,保障核燃料供应,改革开放,多点布局,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
事实上,由于铀资源的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美、欧等核电大国和地区铀资源对外依存度普遍居高不下,均主要来自澳大利园、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尼日利亚等少数几个富铀国家,日本更是95%以上依赖于美、法、英等国,但并未因此而出现铀资源危机。实际上,随着中国日趋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其负责任、建设性的一员,包括铀资源在内的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并不会构成安全隐患,反倒可能成为促进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市场、在更广泛领域内改革开放的外在动力。
第三,关于核废料处理难,核电站退役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均因核废料难处理派生而来,故放在一起来讨论。王老师以近乎恐吓的口气说“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核废料难处理,王老师所言非虚。面对核废料,芬兰人就绞尽脑汁,想出了通过挖掘500米的洞穴,蚕茧一样层层包裹,来予以隐匿的办法,其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但从一个发展主义的眼光来看,其一,核辐射有其安全距离,而地球尚有大面积的无人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尚无法解决核废料无害化处理问题,但可以将其封存,只是其投入应纳入核电总成本一并核算。其二,现有核电技术只是路径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在开展钍基熔盐堆研究。根据中科院规划,2020年-2030年将建成工业示范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倘若成功,则现有技术路径下的核废料将不是麻烦而是资源。
至于核电退役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一方面,王老师所列举的相关成本数字,本身涉及通货膨胀因素,单纯看绝对数字,可能会有误导读者之嫌。此外,王老师所讨论的退役费用占初始投资的比例,窃以为,更应该从一座核电站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考虑其投入产出比。更何况,人们对核电退役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对核电无害化处理的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退役核电数量不断增加,市场需求增大,有理由相信核电退役相关技术革新、相关设备制造的规模化效应将逐步体现,成本曲线会呈下降趋势。
第四,关于内陆核电。
内陆核电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基本属于伪命题。试问,沿海核电可以执行更加宽松的安全标准吗?显然不能。
针对王老师重点谈到的水资源问题,首先,沿海也好,内陆也罢,核电站选址原本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论证过程,对水资源条件(当然也包括地质条件等其他一系列条件)有极为严格的论证。简言之,一个地方如果被选为核电厂址,则其必符合相关要求,否则就是项目可研做没做好的问题,而非核电技术可行性问题。正因为核电选址的高标准,严要求,相关部门才要求部分暂停的内陆项目,须对厂址予以保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地理条件也是稀缺资源。
其次,诚如王老师所言,“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核电对水资源的需求,并非是流域性的(面上的),而更多的是点上的,所以,好比我们并不能因为人均收入不高、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认为中国没有富裕阶层一样,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居然找不到几个、几十个水资源有保障的核电厂址。
所以,王老师关心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把选址工作做得更严谨、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问题,而非一个“是”或者“否”的颠覆性的理由。实际上,核电对于水资源的需求,尽管确实高于火电,但核电的安全运行核心乃在于其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否则,无法解释,福岛面朝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却依然无法避免堆芯熔化的风险。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围绕核电的种种争议,是bad publicity(负面宣传)、邻避效应、糟糕的公众沟通、决策过程缺乏公信力、公共项目补偿机制和利益诉求机制缺失以及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单纯看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公众,其逻辑都可以自洽,但大家各执一词,形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如何解开这个结,专家学者们已经开出了诸多药方,也各有道理。我想谈三个可能在一部分人看来不接地气的建议:
一是鉴于核电的特殊性,建议应该建立形成一个全球核电项目论证机制。在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平台基础上,构建形成全球核电专家库,对全球范围内的核电项目开展一一论证,并作为核电项目启动的前提条件之一,纳入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对于当前我国相关项目决策不够公开透明,或发挥一定的补充和外部支撑作用。
二是公众利益诉求集体谈判机制。逻辑上来说,公众潜在利益受损,均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获得合理补偿,但目前我们缺乏这样一套信息公开、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最终导致利益诉求的表达演变成为情绪化的宣泄。这涉及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公众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与由政府背书的核电企业谈判的问题,需要在观念上和机制上有所突破。
三是核电安全应形成全球安全监管机制。福岛核事故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已经开展了类似工作,但远远不够,也没有日常化。当然,无论是核电项目建设和全球核电安全监管机制,都涉及到一个国际协调和内政边界的问题,但从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治理以及核安全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也许会在广泛层面达成诸多国际共识。
每次提及核电,都忍不住想起英文中的一个词汇,叫necessary devil,即所谓“必要的恶魔”。一如任何事物一样,核电也有其两面性。它给我们带来清洁电力的同时,也一并带来了一些待解的难题。但短短六十几年的历史和区区几次事故,尚不足以说服我对核电投反对票,而更愿意相信它是个“必要的恶魔”,并将彻底驯服它、驾驭它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研究和实践摸索上。
(作者来自:上海燃气(集团)公司)
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
我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但是,随着2013年雾霾治理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在一些报道里,与煤电相比,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电似乎是“满足中国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中国能源环境污染、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现实的、重要的途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加速发展核电、再建80个核电站”等。如果再建80个核电站,核电无疑要往内陆发展了。
治理雾霾,去煤化是无可争议的。但我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理由有四: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3年,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绝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中国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石油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大家就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而且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如果核废料在现阶段已经“可控制、可驾驭”,为什么发达国家要转嫁别国呢?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是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来估计一座百万千瓦的核电站退役资金占最初投资的10%—15%,而法国布雷尼力核电站退役金从2001年占最初投资的26%增至2008年的59%,总金额达到了原始预算的20倍。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全世界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发达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电,所以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退役这个难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2012年6月4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2003—2009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即人类对核电的技术驾驭水平有限、核资源短缺、核废料难以处理、核电退役周期长且成本昂贵、国外内陆核电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前景等因素,核电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洁、更不经济的能源。中国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中国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不能“饮鸩止渴”。本文摘自《中国能源报》
对照核电60余年的发展史,尽管遭遇过切尔诺贝利、三里岛、福岛等几次人祸天灾引起的事故,但核电整体运行安全记录堪称优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燃煤、燃油等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相比,可谓九牛一毛。窃以为,如果人类必须使用能源的话,核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至于王老师期望人类彻底掌控核电,愿望当然良好,但实践领域,恐怕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无论是能源领域、航空领域还是其他各类工业制造领域,莫不如是,难道因此而要让世界退回到农耕文明的小国寡民时代?
 新闻投稿
新闻投稿